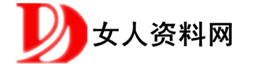周松芳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八大菜系中最流行的非川菜莫属,即便在海外,晚清民国时期一枝独秀的粤菜,现在也应该已退居次席让位于川菜了吧。其实,在民国时期,川菜也有风头直逼粤菜之势,而且出圈(川)也比粤菜更早,故曾作《民国川菜出川记》刊于2018年7月14日的《上海书评》。近三年来,继续发掘一手文献,积累渐多,也更了解晚清民国川菜在全国的发展流行情况,及其赢得“标准国菜”殊荣的故事,故值得再撰一文,谈老上海的川菜馆。以就教读者方家,文献方面,则力避重复引用,有兴趣的读者自可查阅前文。本文为上篇。
聚丰园,《商业月报》 1947年(第23卷 第5期 ,1页)
人言上海川菜馆始于清末:“至光绪三十三年,始有川菜馆一家,名式式轩。”(伯琦《上海菜馆》上,《社会日报》1942年12月22日)至民国渐盛:“自光复以后,伟人、政客、遗老,杂居斯土,饕餮之风,因而大盛。旧有之酒馆,殊不足餍若辈之食欲,于是闽馆、川馆,乃应运而兴。”(严独鹤《沪上酒食肆之比较》,《红杂志》1923年第34期)褚俊达的《上海菜馆之今昔》则点明了这些遗老文酒风流之所在,“集于小有天、别有天、醉沤斋、式式轩诸家”,藉是之故,“闽蜀菜馆之名,因之大噪,士夫商贾之请客者,意非此种菜馆,不足以表盛馔。每筵之价,需十金以外”。(《常识》1928年第1卷第92期)
不过式式轩是否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就出现了,那可不一定;伯琦先生的文章写于1942年,而早在1924年,明弘先生的《尊前琐述》(《申报》1924年12月21日第19版)已说“兴在民国元年”:
川馆之兴,在民国元年,最先有式式轩、醉沤居,而庖丁则均华阳王雪老所造就。天下庖丁治馔,非得主人之指导,决不为功。雪老素尚精美,尤能己出意调味,庖丁承教,造诣自高。其名手凡三:曰王、曰向、曰廖。王厨尝开锦江春,留沪不久,即至香港。向厨历事醉沤、古漏(当为渝之误)、兴华、大雅,今始辍业。廖则由式式而都益,于今不废。就中五六年间,诸遗老带设一元会、朔望会以聚餐,清道人则为之提调。时古渝轩主者何书农亦雅士,每次广筵,必立新意,制佳肴。道人所手书之菜单,凡百余叶(页),饮馔之精,于此为极焉。
详文意,则凡此种种,皆所亲见亲闻,属实不诬。醉沤斋(居)则稍后起,于1913年2月6日试业,19日正式开业:
本斋开设三马路口望平街中,选集川厨,略备乡味,坐次雅洁,招待周全,士女来宾,内外区别,小酌全席,因应咸宜。兹择于阴历正月元旦日先行交易,十三日开张,倘蒙惠顾,不胜欢迎,特此广告。(《醉沤斋广告》,《申报》1913年1月31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第4版)
而在更早的材料中,甚至有说醉沤创办于式式轩之前的:
从前沪妓住家之叫菜,十五年前最著名者为聚丰园,自招商、华商、品商、通源各菜馆相继列肆,住客叫菜,隐然为各家专利。辛亥而后,川闽各菜馆如醉沤,如式式轩,如别有天,如小有天,次第崛起,一般老饕,若有同嗜,于是招商等各家有天然淘汰之象,近则尤以别有天、小有天两家最流行云。(横山《海上花丛之沿革》之《菜馆之新陈代谢》,《小说新报》1915年创刊第1期,第6页)
至于说醉沤或式式轩庖丁均为王雪老王秉恩所造就,虽然查无实据,也属事出有因——早期上海闽川菜馆,既为遗老所好,王秉恩自然也属其列,而且这些馆子或许因此之故也都追求“文艺范”,醉沤之名与联,就属典型:
小花园昔有川菜馆曰醉沤者,其牌号至为奇辟,且不易了解。其客厅有四字楹联句云:“人我皆醉,天地一沤。”嵌字非常熨贴,并不啻为该号商标下一注脚。该馆顾客多达官闻人,想系名家手笔。附近有都益处亦川菜馆也,中有联云:“为厌珍羞,且思芦蛤;惟有海月,可敌茘支。”造语峭拔,不落恒蹊。(海云《沪上商店之楹联》,《申报》1926年1月28日第18版)
包天笑还将这一名联及餐馆用作了他的小说场景:
祖书城道:“就在这里望平街上有一家四川馆子唤做醉沤,我们就到那里喝三杯以御寒气。古人诗云:‘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正是为今天咏的了。”……便同苏玄曼两人出了平报馆到望平街这一家醉沤川菜馆来。只见门前一副银杏木绿字大对联,上联是“大地一醉”,下联是“浮生如沤”。(钏影《海上蜃楼》第十三回《编歌剧汪伶叹孤诣 研梵文苏子译新诗》,《申报》1924年12月19日第17版)
之所以传言王秉恩参与开创海上川菜事业,还有一大因缘,即其不仅为海上遗老,也还是川帮大佬呢,由下面一件事即可见出:“旅沪川人王秉恩等近组四川善后协会兹将其简章公电录下……”(《川人组织四川善后协会》,《申报》1919年4月12日第10版)而且广受社会尊敬,在他去世多年后,在驻美大使施肇基的侄子与其侄女王藜青的离婚案中,报章犹称:“王女现年三十三岁,系出名门,为已故前清广东臬台王秉恩(字雪岑又名燮丞)之女。”(《施家吉妻诉请离婚讼案》,《申报》1935年7月12日第12版)至于郑逸梅、徐卓呆径直说醉沤王秉恩所开,则是后出文献,不足为据了。(郑逸梅、徐卓呆《一称报馆街的望平街》,载《上海旧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而之所以多唠叨几句王秉恩,也是想着各大菜系在形成以及走出本土的过程中,文人和文化的力量实在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先导的力量。试想粤菜如果没有广州的太史菜和北京的谭家菜,能有后来的“食在广州”的局面?论饮食的豪侈,屈大均说天下食材粤东尽有之,赵翼说平生最肥缺莫过广州知府任,府中饮食,虽钟鸣鼎食无以过,方此之际,为何没有“食在广州”的传说?笔者曾一再撰文认为,“食在广州”的真正扬名,源于上海媒体及文人的宣扬。再则湘菜如果没有谭延闿的谭府菜,川菜在本土没有姑姑筵及一众名士的追捧,也难以顺利成长为一大菜系。
上海作为移民城市,人口构成更新快,餐饮业的更新换代也受影响,所以到二十年代,似乎已是都益处一领风骚了:“沪上川馆开路先锋为醉沤,菜甚美而价奇昂。在民国元二年间,宴客者非在醉沤不足称阔人。然醉沤卒以菜价过昂之故,不能吸收普通吃客,因而营业不振,遂以闭歇。继其后者,有都益处、陶乐春、美丽川菜馆、消闲别墅、大雅楼诸家。都益处发祥之地,在三马路(似在三马路广西路转角处,已不能确忆矣)。其初只楼面一间,专售小吃,烹调之美,冠绝一时,因是而生涯大盛。后又由一间楼面扩充至三间。越年余,迁入小花园,而场面始大。有院落一方,夏间售露天座,座客常满,亦各酒馆所未有也。” (严独鹤《沪上酒食肆之比较》,《红杂志》1923年第33期) 梅生《上海菜馆之今昔》(《申报》1925年11月10日17版)也反映了上海川菜馆的更新迭代:“今醉讴斋、式式轩已闭歇,蜀菜馆之新起者有都益处、锦江春。”
本馆向在上海三马路筱花园,开设十有余年,菜点之精,素蒙绅商学各界人士推为川菜馆中之鼻祖,所以顾客盈门,嘉宾满座。今因原址房屋翻造,迁移于爱多亚路中大世界东首新建三层楼洋房……择于本月初八日正式开幕。(《都益处川菜馆近迁移声明》,《申报》1924年9月2日第1版)
这里最重要的是点出了二十年代初期六七家重要的川菜馆,当时的城市指南书,所载录的川菜馆,也不出这几家,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22年版《上海指南》载录有大雅楼(汉口路二五三号二五四号)、美丽慎记川菜馆(汉口路一三九号浙江路口)、消闲别墅(广西路四三九号)、陶乐春(汉口路二四一号)、都益处(浙江路小花园七号)5家;到商务印书1930年版林震编纂的《上海指南》,名单略有变化,也只大雅楼(福州路二三一号)、共乐春(北四川路一九七O号一九七一号)、美丽慎记、陶乐春(汉口路二四三号)、都益处(爱多亚路一六二号)、聚丰园(广西路小花园口)6家,而仔细一比较,则同一名号下面,地址确有变化。《申报》1922年11月2日第18版的《菜馆一览》,于“川菜”开列三家:“兴华川 汉口路浙江路转角 中一二七八;美丽川 汉口路浙江路转角 中一三六二;大雅楼 汉口路浙江路转角 中三九七四。”兴华川菜馆,则未曾经人道及,事实上可能还挺不错,因为奉贤知县宴客都假座此处:“前任川沙调署奉贤之赖知事,以息借冬漕,迭奉委提,本籍绅董,平日在沪居,多昨特来沪,假兴华川馆宴客,藉以商借报解云。”(《奉贤县知事来沪宴客》,《申报》1920年8月19日第11版) 如此则诚属遗珠。
新出的《上海饮食服务业志》说还有一家川菜馆名店东亚饭店,1917年开设于南京东路680号,以小吃双菇翠包、荷叶糯米等著称,大约是后来转型的吧,因为其虽然颇有见于当年文人笔端,但没人把它当川菜馆看。(《上海饮食服务业志》第一篇《饮食业》第七章《名店名师》,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版)事实上是否川菜馆还值得考辨,因为有一家著名的粤菜馆也叫东亚饭店。
因为时兴,创办者多,他们还成立了川菜馆同业公会,并不断联合抬价,也可见其早期兴盛之斑:
启者:敝业开创以来,荷蒙各界欢迎,无任钦佩。近因各物昂贵,售价不敷成本,是以同业公议于开市日起一律改售大洋,伏希各界光顾为荷。都益处、陶乐春、兴华川公启(《上海四川菜馆同业公议新正月初五日开市一律大洋》,《申报》1920年2月23日第1版)
启者:迩来敝业百货步步腾贵,兼以缴费浩大,实不能支,爰是邀集同业公议,自中秋节后每席加洋一元,以补血本,而图久远,伏祈光顾,诸君鉴谅,是幸。都益处、美丽、大雅楼、陶乐春同启(《四川菜馆同业增价声明》,《申报》1921年9月20日第1版)
所谓不敷成本,借口耳!早期川菜馆之贵,是历来人所公认的。这一点开头已有所提及,兹再补一则材料,如王定九《上海顾问》说:“像平菜近十元的酒筵,已很可宴客,但川菜,必须十五六元。”(中央书店1934年版,第220页)
这些川菜馆中,陶乐春倒值得特别提起,因为他似乎是鲁迅的最爱之一;1927年10月3日从广州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去了陶乐春,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6月,共受邀去此店饮宴6次,请客者分别有李小峰、郁达夫和内山完造等:
1927年10月3日:(抵上海)下午同广平往北新书局访李小峰、蔡漱六,柬邀三弟,晚到,往陶乐春夜餐。
10月16日:夜小峰邀饮于三马路陶乐春,同席为绍原及其夫人、小峰夫人、三弟、广平。
1927年4月2日:达夫招饮于陶乐春,与广平同往,同席者国木田君及其夫人、金子、宇留川、内山君,持酒一瓶而归。
1929年1月26日:午达夫招饮于陶乐春,与广平同往,同席前田河、秋田、金子及其夫人、语堂及其夫人、达夫、王映霞,共十人。
1929年3月17日:晚同柔石、方仁、三弟及广平往陶乐春,应小峰招饮,同席为语堂、(林)若狂、石民、达夫、映霞、维铨、馥泉、小峰、漱六等。
1929年6月20日:晚内山延饮于陶乐春,同席长谷川本吉、绢笠佐一郎、横山宪三、今关天彭、王植三,共七人。
当然,其他川菜馆鲁迅也去过好几家,如都益处:“1928年2月9日:晚同三弟往都益处夜饭,同席十五人。”再如消闲别墅:“1928年2月12日:午前章锡琛招饮于消闲别墅,与三弟同往,同席九人。”其实1925年8月30日,鲁迅经上海赴厦门大学任教时,即与同样经上海赴清华国学部任教授的朱自清相逢于消闲别墅,出席文学研究会同人郑振铎、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锡琛、刘叔琴和周建人等组织的饯行公宴。(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鲁迅还去了美丽川菜馆:“1928年2月29日:晚伏园来。林风眠招饮于美丽川菜馆,与三弟同往。”而朱自清1925年8月22日初抵上海即偕叶圣陶、方光焘共饮于此。(《朱自清年谱》第52页)
另古益轩和聚丰园鲁迅均分别两去:
1929年8月27日:晚蒋径三招饮于古益轩,同席十一人。
1932年10月5日:晚达夫、映霞招饮于聚丰园,同席为柳亚子夫妇、达夫之兄嫂、林微音。
1933年3月30日:晚往聚丰园应黎烈文之邀,同席尚有达夫、愈之、方保宗、杨幸之。
1934年1月6日:午烈文招饮于古益轩,赴之,同席达夫、语堂等十二人。(陈漱渝等编《鲁迅日记全编》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7页、53、89、93、102、47、48、155、245、272、313页)
官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的邵元冲及其作为神州女学和神州日报创办人的妻子张默君,二三十年代每至上海,必吃川菜,诚如他们1924年10月1日在美丽川菜馆晚餐后,“饮噉既豪,复佐以娓娓清谈,逸趣豪情,足为他日追忆之资,又此间红烧蹄殊美,足快老饕”,那他们的上海川菜记忆,也的确应该胪记于下,以与读者分享:
1924年11月19日:午间至都益处,应雨岩午餐之招,同席有协和、耿和生、但怒刚及粤中同来诸君。
1924年11月21日:午间偕至都益处,川菜馆,应黄贻荪伉俪午餐之招,兼晤杨杏佛夫妇。
1928年6月19日:午间应王伯秋之约至美丽川菜馆午餐,同席有寿毅成、胡适之、董鼎三、宋阜南诸君。
1928年6月21日:午间偕默应毅成、鼎三美丽川菜馆午餐之约,同席有胡朴安、王伯秋诸君。
1928年12月3日:午间约文德、逸云在美丽午餐。
1929年1月13日:午约季陆及何叙甫、郭复初、郑毓秀等在都益处午餐。
1935年12月10日:傍午偕默及祝尧人外出,午餐于小花园川菜肆,制馔尚精洁。(《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77、78、433、434、479、498、1344页)
观其与席者,既有文人墨客,也有达官贵人,邵氏夫妇本身也即文人兼官员,大有名于时,自然当得起上海川菜馆的美好记忆。而其去得最多的美丽川,也是梁实秋和徐志摩等念兹在兹的川菜名馆;梁实秋大约当时年纪尚属稚嫩,都到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之际”了,还说“那时候四川菜在上海初露头角”,而且念念至老的不过一道蚝油豆腐:
李璜先生宴客于上海四马路美丽川(应该是美丽川菜馆,大家都称之为美丽川),我记得在座的有徐悲鸿、蒋碧微等人,还有我不能忘的席中的一道“蚝油豆腐”。事隔五十余年,不知李幼老还记得否。蚝油豆腐用头号大盘,上面平铺着嫩豆腐,一片片的像瓦垄然,整齐端正,黄澄澄的稀溜溜的蚝油汁洒在上面,亮晶晶的……我首次品尝,诧为异味,此后数十年间吃过无数次川菜,不曾再遇此一杰作。我揣想那一盘豆腐是摆好之后去蒸的,然后浇汁。(梁实秋《豆腐》,载《雅舍谈吃》,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徐志摩说的美丽川故事,最为脍炙人口,堪称经典:“(十一日)方才从美丽川回来,今夜叔永夫妇请客,有适之、经农、擘黄、云五、梦旦、君武、振飞,精卫不曾来,君劢闯席。君劢初见莎菲,大倾倒,顷与散步时热忱犹溢,尊为有‘内心生活’者,适之不禁狂笑。君武大怪精卫从政,忧其必毁。”“十五日:前日沫若请在美丽川,楼石庵适自南京来,故亦列席,饮者皆醉。适之说诚恳话,沫若遽抱而吻之——卒飞拳投詈而散——骂美丽川也!今晚与适之回请,有田汉夫妇与叔永夫妇,及振飞,大谈神话。”(《儒林新史之一页》,《论语》1936年8月1日第93期,第6、8页)这些可都是顶级名流啊!
胡适自己也写到这一节:“(1923年10月13日日记)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这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胡适平素的日记都很详细,但记饮食很简略,尤其是在国内,更鲜少记,因此这条材料便很有意思了;粗略翻检,又找出另两条胡适上川菜馆的日记,附记于右:“1921年8月26日:到都益处吃饭,主人为郑来[莱]。”“1929年9月23日:晚间在古益轩吃饭,主人为汪孟邹,主客为江彤侯。”(分见《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册第448;第四册第72页;第五册第523页)
另一个学界大咖顾颉刚也留下了不少上海川菜馆的诗酒文会的名流记忆:
1923年12月4日:致觉、颂皋、为璋邀宴于广西路消闲别墅。
1926年8月12日:到美丽川菜馆吃饭……晚饭同席:乃干、雪村、伯祥、圣陶、愈之、予同。
1927年9月2日:到四马路古益轩赴宴……今夜同席:叔平先生、树平、乃干、何静山、予(以上客),顾鼎梅先生(主)。
1927年9月10日:到聚丰园赴宴……今晚同席:谭熙鸿夫妇、莘田、吴家瑞女士、静山、钱贞元女士、金家懋、毛又文女士、程本正、蒋梦麟先生、予……(以上客),张伯芩、凌济东、查勉仲(以上主)。
1927年9月17日:到聚丰园赴宴……今晚同席:龙文、四穆、周命新、陈仲明、刘奇(子行)、冯炳奎(楚碧)、予(以上客),缪金源(主)。
1929年3月2日:到适之先生处,并晤梁实秋。邂逅梁式湘,同到天韵楼。到聚丰园吃饭。
1929年3月22日,上海:不广先生邀至聚丰园吃饭,同座为适之、旭生两先生及孟真、予等。
1936年2月6日:应雪村约,到聚丰园川菜馆……今晚同席:沈从文、王鲁彦、巴金(李芾甘)、李健吾、郑振铎、周予同、孙祖基、予(以上客),章雪村、夏丐尊、丁晓先、范洗人、徐调孚、王伯祷(以上主)。
1937年1月20日:到锦江春吃饭……今午同席:俞颂华、胡仲持、子臧、予(以上客),荫良(主)。
(《顾颉刚日记》,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一卷第425、779页,第二卷第82、85、87、258、264页,第三卷第439、558、592)
比较而言,上海的川菜馆中,如果鲁迅的最爱是陶乐春,顾颉刚的最爱则非聚丰园莫属了;聚丰园也属当时的川菜新贵:“海上近日崛起两大川菜馆,一为广西路小花园之聚丰园,一为跑马厅之南洋菜社。聚丰园日昨宴客,系由余大雄君代邀,肴馔美绝伦。席间飞花醉月,极为热闹。南洋菜社前夜宴客,系由步林屋君代邀,治馔亦精,来宾尤众。(《海上近日崛起两大川菜馆》,《琼报》1928 年11月26日第2版) 多少年后,唐振常先生还说“聚丰园为大众化川菜的代表”。(唐振常《乡味何在》,载《雍飧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此外古益轩也应当是有地位的:“前晚两路局长李垕身君设春宴于三马路古益轩川菜馆,宴集两路同人,共设九桌,餐室陈列兰花不少,吐为王者之香,沁人心脾。(《琼报》1928年2月19日2版)
在后来最著名的川菜大腕锦江川菜馆老板董竹君看来,无论陶乐春还是聚丰园,“因其味过浓,麻辣又重,故座上客除少数四川人外,当地人很少光顾,因而生意清淡,盈利不多,有时还会亏本停业”。(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7页)难道鲁迅和顾颉刚都是重口味?而从顾氏1945年7月14日在重庆的日记中所说:“陈裕光告我,常吃维生素C,可治伤风感冒。又有人说,多吃辣子可不生湿气,予尚能吃豆瓣酱,此后当常吃。”则其能辣的程度并不高。(《顾颉刚日记》第五卷,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497页)当然也有可能发展到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初期,川菜的口味日趋麻辣,但传统的早期的川湘菜都是不辣的,也才有早期闽川菜馆的并称。即便是抗战时期,也即便是最嗜辣的重庆,正式的高档一点的宴客还是不辣,著名作家张恨水即有现场的观察:“至于饭必备椒属,此为普通现象,愚亦嗜辣,与川人较,瞠乎其后。唯川人正式宴客,则辣品不上席。江南人有应川人之约者,固不必以椒姜为惧耳。”(张恨水《重庆旅感录》,《旅行杂志》1939年第13卷第1期,第51页)
也好,那你董竹君就去开一间传统的味道清淡的川菜馆吧。果然,1935年3月15日董竹君在法租界大世界附近的华格臬路上开办了锦江小餐(即锦江饭店前身),依倚特殊背景,一开业就顾客盈门,座无虚席,“连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以及南京政府要人和上海军政界人物来吃饭也得等上很久”。后来杜月笙更帮助她“扩充了大小雅座十几间,散座二十多桌的大小餐厅各一间,总共能容纳三百人左右,扩大了好几倍。办公室有了三四间。储藏室、预备室等也添设扩大,工作人员增加了好几十人,改名锦江川菜馆”。(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第251、253页)锦江的清淡,从它后来的行政总厨、著名的粤菜大师肖良初被视为川帮大师,即可见一斑。(详参拙文《上海粤菜厨师的国宴之路》,《档案春秋》2015年第8期)
但这个时候,能与锦江相抗的川菜馆,有蜀腴和小花园等。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每到上海,喜食川菜,有的报章则径直揭诸标题——《于院长到沪喜食川菜》(《民报》1937年1月4日第1版):“闻于氏日来喜食川菜,昨午又赴广西路某川菜社,系应中委张静江之弟之邀约云。”按图索骥,或即蜀腴,因为是年元旦,新开于此:
本埠广西路小花园对过新设蜀腴川菜馆,为上海川馆之巨擘,设备精雅,招待周挚,特雇名厨烹调,极南北清腴之味,允于蔬菜独擅特长,大宴小酌,无不相宜。馆主徐君鹤轩,尝谓国菜之特点,在腴者使之清、清者使之腴、惟川菜差能表征。兹以廿余年精研所得,贡献社会,其伟愿在发扬国光,非寻常牟利者可比。故其定价极廉,且特用小盘,以便小酌,一洒川菜巨簋价昂之积习,要使顾客以最轻微之代价,得极美满之结果。闻已定于二十六年元旦开慕,预定房闲座位,极为踊跃,前途发达,不卜可知也。(《蜀腴川菜馆元旦开幕》,《申报》1936年12月31日,第14版)
川菜馆既风靡一时,那到底当时吃些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而向来研究者于此并不着力,这里我也是简单发掘一下,以为抛砖引玉。 比较早介绍到四川菜馆菜谱的是1924年12月21日《申报》上署名熊的《上海菜馆之鳞爪》:
四川馆宴客为近来上海最时髦之举,川菜馆亦确有数味特殊之菜颇合上海人之口味而为别帮所不能煮者:奶油鱼唇、竹髓汤、叉烧火腿、四川泡菜等皆川菜馆之专利品也。
1925年版的《上海宝鉴》则更详细开列了当时川菜馆的四时菜单:
常时之炒菜:炒肉片、椒盐虾糕、辣子鸡片、加厘虾仁、炒橄榄菜、炸八块、虾子玉兰片;烧菜:米粉牛肉、米粉鸡、白炙脍鱼、酸辣汤、奶油广肚、红烧大杂烩;其他:云腿土司、酸辣面、鸡丝卷。
春季之炒菜:虾子春笋、凤尾笋;烧菜:清炖时鱼、红烧春笋、叉烧黄鱼、火腿炖春笋;其他:蛋皮春卷。
夏季之烧菜:大地鱼烧黄瓜、白汁冬瓜方、清炖蹄筋、鸡蒙缸豆;其他:冰冻莲子。
秋季之烧菜:奶油白菜心、红烧安仁、蟹粉蹄筋。
冬季之炒菜:炒羊肉片、松子山鸡丁、炒山鸡片、雪菜冬笋、炒野鸡片;烧菜:四川腊肉、锅烧羊肉、烧踏菇菜、火腿炖冬笋;其他:菊花锅。(王后哲辑《上海宝鉴》,上海世界书局1925年版,第十四编“饮食指南”)
从菜名上看,这些菜多不辣,而且烹制要求相对精细,宜其受欢迎且价昂贵。不过“丰俭由人”,也有人从各川菜馆专门拣出了一些“价廉物美”的菜单,而且还对各菜有相对详细的介绍,这就更可贵了:
川馆中,炒菜比别处好些,即以平常的炒鸡丁一样,都比他处嫩点。诸位点菜,如油焖鸡呀、粉蒸牛肉呀(略加点辣椒粉)、奶油玉兰片呀(笋名)、虾米四季豆呀、冬菜炒肉丝、黄焖肉等,还有一样爆丑腊肉,味道呒啥。听说这几样,真正是地道川菜呢。
川人家常考究的菜,如虫草(补品名)炖鸭子,其烹灶用虫草几许,多少听便,贯入鸭之腹内,细火清炖,盐宜少,若喜重油者,加肉若干。
豆花这样东西,清洁非常且为素品,热天尤宜,惟烹调麻繁(烦),川人极喜食之,这几天三马路陶乐春共乐春,大约已经上市了。(芳尘《川菜之小供献》,《荒唐世界》1927年6月10日2版)
时人在综述上海的菜品时,认为“川菜里面,有几样冷盆,颇为适口,一件是辣白菜,是用辣茄和交菜配成的,味嫩而清口,爱吃的人很多。别家虽然也有仿制,可是总不及川菜馆的鲜美。还有一件是醋鱼,用极久的火候,煮鱼骨酥透,所以吃来酥软异常无骨鲠之虞,而味道也因着火候到家的缘故,很是入味……其他热菜当中,如红烧狮子头、奶油菜心、神仙鸡、纸包鸡等几种,也是拿手杰作。”(使者《上海的吃》之三,《人生刊》1935年第1卷第5期)然而,从这些“杰作”的名称上看,似已无昔日的贵气了,也是为了因应经济的下行,走向价廉物美的新繁荣吧。你看,以新贵着称的蜀腴公开提倡说“其宗旨非寻常牟利者可比,故其定价极廉,且特用小盘,一扫川菜巨盆价昂之积习,要使顾客以最轻微之代价,得极美满之结果”。(《蜀腴川菜馆元旦开幕》,《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12月31日第14版)其所推介的菜谱,也确实非常众化:
蜀腴川菜馆,取最新式之设备,开放冷气,故虽值炎暑,而食客盈门。所制新肴,层出不穷,如青椒生炒鳝片,茄子焖田鸡等品,均甚别致。(老饕,《晶报》1937年7月12日第3版)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