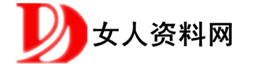赛·托姆布雷在自己的画《维纳斯和阿多尼斯( Venus and Adonis)》 (1978)前。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赛·托姆布雷就在巴黎Yvon Lambert画廊举行过个展,当时法国反响热烈,罗兰·巴特、菲利普·索莱尔斯等人都曾撰文评论。时隔多年,托姆布雷的风潮再度席卷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此次也借展览之机,集结各方学术力量再度解读托姆布雷与巴黎和欧洲的多重渊源。此前,法国Seuil出版社已将罗兰·巴特为托姆布雷撰写的两篇长文结集推出单行本。
《托姆布雷》,罗兰·巴特著。伊凡·朗伯特出版社(Yvon Lambert, Ed.)
像孩童般涂鸦
塞·托姆布雷《无题(纽约市)》1968
赛·托姆布雷的画作给人的直观印象大抵是:随意而为的潦草书写,类似花体字的素描以及涂鸦组成的抽象图案。“弯弯曲曲的笔触,随意的涂抹”正是托姆布雷最为鲜明的创作特质。
赛·托姆布雷偏爱线条,他曾说:“线条是画布上最美的,一种具有强调性的效果”,正是凭借充斥画面的大量线条,托姆布雷模糊了涂鸦和绘画之间的界限。他在1966年到1971年创作的代表作中,灰色的水彩底上用白蜡笔画成的弯曲线条,令人联想到学校黑板上粉笔的随手涂写;而后期的《无题之酒神(Untitled-Bacchus)》,鹅黄色的温暖背景上腥红色的圆圈相互缠绕,像旋风席卷而来又呼啸而过。艺术批评家科克·瓦内度(Kirk Varnedoe)曾说,“托姆布雷影响了众多艺术家,也为难着艺术批评家。他的画作不仅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是难以理解的,仅从艺术史上战后艺术复杂的初期发展阶段考虑它们,同样也难以理解。
《无题之酒神(Untitled-Bacchus)》2005
或许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托姆布雷的创作灵感与他于1954年曾服役于美国空军作为密码员有关。为了快速的破解密码电报内容并传出信号,托姆布雷练就了一手速记功夫,学会如何在黑暗中绘画。这些训练无疑为他日后笔迹潦草的创作风格埋下了伏笔。但是对于那些心甘情愿于托姆布雷画作前长久地驻足的观众而言,画面上一丝一毫的痕迹都展现出托姆布雷作为抽象艺术家绝佳的图像布局能力,以及他如哲人般充满智性的斟酌。
以现代艺术语言对话古典文明
不同于大多数现代派抽象画家,赛·托姆布雷的创作具有很浓的古典主义意味。虽然出生和成长在美国,托姆布雷却与欧洲和地中海结缘甚深。对古典的冥想是贯穿托姆布雷一生作品中的隐秘部分,而他的旧世文明的情怀其实早在青年时代求学初期就已经养成。在1940年代,20岁出头的托姆布雷开始接触抽象派画家罗斯科和波拉克等人的作品,此后他亲历了纽约战后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还有幸得到学长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帮助,在50年代初进入当时美国的先锋运动大本营,位于卡罗莱纳州的黑山学院求学。
年轻的托姆布雷
在这个现代音乐、绘画、摄影、诗歌等诸多文艺形式滥觞的乌托邦乐园,托姆布雷一边跟随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先锋人物弗兰茨-克兰因(Franz Kline)等人学习绘画,一边汲取文艺界激荡的先进思潮。这期间,他与劳森伯格一起读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文化指南》,维吉尔的诗歌、帕萨尼亚斯(Pausanias)的《希腊志》以及早年游历日本的菲诺罗萨(E.Fenollosa)论述日本艺术的书籍……这使他在艺术生涯的早期就深深地沉淀在广博的文明图景之中。1952年,托姆布雷结伴好友劳森伯格一起到北非和南欧旅行,而第一次的旅行似乎成为了他的寻根的还乡之旅。1954年,旅行中的托姆布雷被美国空军召回作为密码员服役。三年兵役期满后,托姆布雷带着一手超现实主义的密码术,毅然离开了纽约,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欧洲继续他的艺术创作。
在实验艺术的大本营,黑山学院师生正在上课
对古地中海历史、地理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史诗的痴迷所蕴育的古典气质在托姆布雷的创作中持续发酵,定居意大利后,托姆布雷的作品中飘忽出一种神秘主义,各种隐喻常见其中。当观众试图理解托姆布雷在1975年创作的《阿波罗与艺术家》这组巨大但画面如同草稿似的绘画时,仿佛在做寻宝游戏——最初,他们或许不明白画中用蓝色的粗体字书写的“Apollo”指代的何物,它可以是古希腊罗马的那一位特指的神,也可以是任何一位古典神,甚至是航天飞船阿波罗11号。托姆布雷在画中留下一系列线索去引导观众去探寻他的意图。他画了些月桂叶,象征着头戴花环的阿波罗神;一些分散在画面的音符符号,意指掌管音乐的神阿波罗,甚至连蓝色的字母也别有用心地暗示神的地中海起源。当然,这个作品所要呈现的不单是阿波罗这一主体,正如画作名字《阿波罗与艺术家》,“艺术家”隐藏在了画作中间,观众在寻找并理解画中的阿波罗的过程变中,最终成为了那位艺术家。
《阿波罗与艺术家》,1975
在创作后期的作品中,文字与图像的相得益彰更成为了托姆布雷作品中最绝妙的隐喻。托姆布雷认为2007年和2008年的花朵母题如“玫瑰”系列(The Rose)和无题的“牡丹”系列(Peony Blossom Paintings)的创作是自己所享受的最自由的一种状态,在“牡丹”系列的最后一部分,黄色的背景中正绽放着鲜红色的花朵,背景里书写的是日本著名俳句诗人松尾芭蕉的诗作。牡丹的盛开是瞬息生命绽放的顶点同时也隐射着随之而来的衰败,而日本的俳句也是对生命瞬间的捕捉和呈现。
《玫瑰》系列之一,2007
艺术界将托姆布雷誉为“现代世界最后一位古典主义者”。但从视觉上而言,托姆布雷无疑又是最善于打破常规的当代艺术家之一。“怀旧”与“现代主义”是托姆布雷创作中同时存在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难以割舍的古典情结以及对于充满图像志意义的关于绘画的完整体系的怀念,使托姆布雷的创作中充满古典的沉思;而另一方面,托姆布雷也深知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描绘的那种现代性:“对于他(现代生活的画家)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的永恒……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这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在艺术形式上,没有谁比托姆布雷更敢于打破规则,他所作的就是凭借那些独创的“虚构的物体”,激活艺术介质,完成其对文化与历史回忆的介入。托姆布雷以现代艺术语言对话古典文明,他将史诗般的事件和个人化的表现注入画面之中,呈现出的是赤裸的直白、层叠的隐秘、无解的晦涩以及个人的记忆与历史的遗忘不断纠结的过程。
《牡丹》系列之一,2009
“粗鲁的”的学院派画家和诗人
以诗歌和古典学作为自己绘画的注脚,托姆布雷的作品里不间断地可以看到诗歌体裁的介入:在古希腊诗人卡图卢斯和荷马启发下,托姆布雷创作出《在伊利亚姆的50天(Fifty Days at Iliam)》;在1985年完成的作品《感伤绝望地看待玫瑰》中,他引用里尔克、鲁米和兰帕德的诗描绘出了死亡和重生的韵律;最为著名的还有他受英国诗人TS·艾略特的诗《四个四重奏》和《荒原》为灵感线索创作的《四季》。
《四季(Quattro Stagioni: Primavera, Estate, Autunno, Inverno)》1983-1995
或许我们应该将托姆布雷视为一位以画作诗的艺术家,他不仅从诗歌中汲取创作资源,并且也时常在画布上画下诗歌的段落。艺术批评家乔纳森·琼森评价道,托姆布雷是一位能够教你回到诗歌中去阅读的艺术家。“我们极少有人像托姆布雷一样阅读,将自己沉浸在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诗歌里,并引逗观看者追随他以懒散的着色在画作中做出高深莫测的引述。”乔纳森回忆自己初看托姆布雷的画作《海洛和莱德罗》(Hero and Leandro)的景象,“它描绘的好像是几抹血腥的红色向海浪激起的白蒙蒙的泡沫发动进攻,在我看来就像是水中的血迹。直到后来,我读了马洛的诗《海洛和利安德》才恍然大悟。诗是这么开头的:‘在赫勒斯滂,真爱之血有罪……’”
《海洛和莱德罗》(Hero and Leandro),1985
托姆布雷或许是近代画家中最“有文化的”,他自己饱读诗书,也期待欣赏艺术的观众能够如此。他的画仿佛在质问观众,你难道没读过卡图卢斯和卡瓦菲斯的诗歌?托姆布雷对于文化的信仰传统而坚定,但是他的创作却并非是沉静和克制的。蜡笔的挥砍、猛掷的溅污,疯狂的涂鸦,咆哮般的红,充满爱欲的淤紫,还有那些神秘的文字,这些元素都常现于托姆布雷的画中。指引托姆布雷的古典精神正是罗马的巴库斯精神(酒神精神),托姆布雷以“身体的血”和“眸中之火”创作,借助历史和神话,抒发隐秘的私人情绪,思考着“性”、“死亡”和“渴望”等问题,最后将情感投射在巨幅画布之上。
丽达与鹅, 1962(罗马壁画上神祇的故事被托姆布雷用淫秽的粉色污迹表示的臀部和乳房再次讲述)。
托姆布雷把优雅和迷狂,细腻与生猛一齐都揉碎在他如诗如画的创作中。“他的艺术始终贯穿着一种文明与野蛮间的张力,他的粗鲁与他的学院派气质共存……,这也正是使得托姆布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天才的原因。”
抽象的另一重维度:想像的现象学
观众正在欣赏赛·托姆布雷的画作
赛·托姆布雷(Cy Twombly)绘制于卢浮宫古希腊青铜展厅天花板上的作品《The Cei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