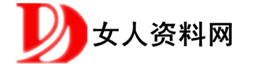吕友仁 | 文
一、“我的夫人”满天飞
《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28日第12版载有李蕴昌的文章,标题就是《我的夫人扬沫》;白岩松撰写的《全方位球迷》中说:“我的夫人也是球迷。”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宋世雄说:“在我取得的许多成绩中,我的夫人对我的帮助很大。”(见谈健《夫人眼中的宋世雄》,载《中国读书网》)2002年7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载有范宝龙《泰思河畔“清华之家”》一文,其中有云:“早在1998年初,我的夫人冯梅在清华毕业5年之后,来这里攻读博士学位。”这些都是见诸文字的,至于诉之口头的,那就无法统计了,所以我说是“满天飞”。
“夫人”一词,古今都能用,问题是用的场合有讲究。“夫人”只能用于他称,不能用于自称。说得再明白点,只能说“您的夫人”、“他的夫人”,不能说“我的夫人”。“夫人”是尊称,而尊称只能用于他人,不能用于自己。这是几千年的老规矩,老传统。《论语·季氏》:“邦(一本作“国”)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礼记·曲礼下》:“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孔颖达疏云:“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唯诸侯得称,《论语》曰‘邦君之妻,邦人称之曰君夫人’是也。”难道上文执笔诸公都是以诸侯自居的吗?我想不会。《明史·职官一》记载:“外命妇之号九:公日某国夫人。侯日某侯夫人。伯日某伯夫人。一品曰夫人,后称一品夫人。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清代外命妇的称号,大体与明代相同,具见《清史稿》卷110,此不赘。由此可知,只有封爵是公侯伯的妻子和一品、二品大员的妻子,才有资格被封赠为“夫人”。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公侯伯的妻子和一品、二品大员的妻子有资格被皇帝封赠为夫人,并不意味著这些大员在对外的场合就自称其妻子为夫人。
清末粱章钜写了一部《称谓录》,该书卷5在“对人自称妻”下面,一共列了六种称呼:“内、内子、内人、室人、荆妇、山妻”,唯独没有“夫人”一词;而在“称人之妻”下面则列有“夫人”一词。这说明,至少从孔夫子到清末,“夫人”总是用于他称的。
在今天林林总总的辞书中,我认为,惟有《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对“夫人”的释义是正确的:“古代诸侯的妻子称夫人.明清时一二品官的妻子封夫人,后採用来尊称一般人的妻子。现在多用于外交场合。”说的是“尊称一般人的妻子”,恐怕不包括自己的妻子在内。
再翻看《汉语大词典》对“夫人”的释义,共有五个义项,其第五个义项是:“对自己及他人妻子的尊称。”看来,称呼自己的妻子为“我的夫人”是言之有据了。可是且慢,此条释义下边列举的两个书证并不支持这种提法。书证一是巴金《灭亡》第七章:“他底身边坐著他底新婚夫人郑燕华。”书证二是茅盾《子夜》三:“我看见他出去。吴夫人。”两个书证,讲的都不是“对自己妻子的尊称”,而是对他人妻子的尊称。看来,要想从规范的文学作品中找到“对自己的妻子”可以“尊称”夫人书证也很难。蔡希芹《中国称谓辞典》79页:“夫人,对妇女的尊称。《三国演义》第十六回:操曰:‘夫人识吾否?’邹氏曰:‘久闻丞相威名,今夕幸得瞻拜。’操日:‘吾为夫人故,特纳张绣之降,不然灭族矣!’后泛称妻子为夫人。”按:邹氏是骠骑将军张济之妻,地位与诸侯之妻相当,曹操称之为夫人宜也,但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夫人”是“对妇女的尊称”;至于由此而引申出“后泛称妻子为夫人”,则语义含混(“妻子”,谁的妻子?包括不包括自己的妻子?),置之毋论可也。
对他人称呼自己的妻子,一般人,甚至目不识丁的乡巴佬儿,可能用语粗俗,但绝对不会出错。而用词不当的恰恰是高学历的知识份子,言之令人扼腕。窃以为,如果我们要展示自己的谈吐儒雅,“我老婆”、“我屋里的”、“我媳妇”之类的称呼略嫌土气,可以不用;“拙荆”、“贱内”、“糟糠”之类的称呼又迹近迂腐,也可弃置;权衡比较,不妨就称“我太太”,不是也很好吗!《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对“太太”的一个释义就是:“称某人的妻子或丈夫对人称自己的妻子(多带人称代词做定语):我太太跟他太太原来是同学。”或者朴朴实实地来一句“我的妻子”,也十分得体。
二、称名称字乱了套
古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往往不仅有名,而且有字。这个传统,在我们的老一辈中还较多保留著,到了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笔者虚度六十有五),有名有字的人,即令是有,怕也是微乎其微了。可能正是由于少见多怪的原因,于是就出现了称名称字乱了套的现象。这种现象,不少有识之士已经先我而谈到了。例如,周汝昌先生说:“中华读书人(知识份子也),对人不能直呼其名,那最无礼貌了,只称表字。所以当面也好,背后也好,我总称‘启元白’、‘元白先生’——元白是启功先生的表字,但现下很少讲究此礼了。”(见《雅人深致——偶忆与启功先生相交旧事》,载人民网2002年12月29日)
“现下很少讲究此礼了”,此话一点不假。这样的例子很多。《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18日12版栽有刘兆吉《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一文,说的是1929年,刘文典先生任安徽大学校长,由于该校学生闹学潮,教育部下文“传令刘文典,蒋委员长召见”。刘文典发牢骚:“我刘叔雅(按:刘文典,字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这里说“我刘叔雅”云云,恐怕不是实录。身为大学校长的刘文典,不会不知道,自称只能称名,不能称字的道理。
《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孔颖达疏云:“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日‘幼名’。‘冠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礼记·冠义》:“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郑注云:“字,所以相尊也。”《白虎通·姓名》:“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颜氏家训·风操》:“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所以字又叫“表字”。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谓夫子曰仲尼。先左丞(按:谓其父陆佃)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苏季明书张横渠事,亦只曰子厚。”以上所引文献,可以看作是刘文典先生宣称“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的理论根据。
总而言之,称人称字,称己称名,前者表示敬人,后者表示自谦,这是几千年来的老规矩。《礼记·曲礼上》:“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记·表记》:“子曰:‘卑己而尊人。’”这两句话,愿与乱用称谓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