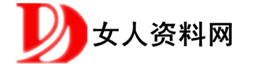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表明文体随时代而变的整体特征。从事实看,这应该是没错的。不过此种嬗变不是断裂式的瞬间过程,而需要长时间的孕育和发展。宋词成就最高,就像唐诗无与伦比,但为词奠定基础的还是唐人,比如温庭筠,比如韦庄。
温韦都是“花间派”代表,风格却迥异,温庭筠词重文饰,语言华美;韦庄词善白描,直白诚挚。试看这句“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似乎过于直白,但正因其真白,才可以瞬间击中一代又一代离家之人的心。
本期“周末读诗”,与你分享的是韦庄的爱情。在两首《女冠子》中,韦庄以率直的言辞表露了自己对女子的深深恋念之情。两首词都写到“梦”,离别让他如坠梦中,他又多次在梦中再见女子,可惜,最终醒来,“知是梦,不胜悲”。韦庄的词因直率而易读,却不失词味,白描几笔,勾勒的情景却可感可触,他的婉转哀愁就附着在这情景中,因此也可感可触了。
撰文 | 三书
农历四月十七,并非某圣贤的诞辰或祭日,亦非法定或俗成的假期。这一天只是个因普通而安静,因无为而端丽的日子。它被晚唐诗人韦庄铭记,是因为在四月十七这一天,他曾与爱人生离死别。
离别就是死去一点点
《女冠子·其一》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
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
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离别,就是死去一点点,是对往昔所爱的一种死去。离别不仅是与他人作别,而且也意味着,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或一个自我割舍。而那被割舍的,仿佛已拥有了独立的生命,虽被割舍,却不会立刻死去。它会在断处呐喊,在风中哭泣,无所归依。它疼痛的回声可以传得很远、很远。
而就在你觉得过去已经过去时,一个梦、一个声音、一种气味、一个数字或一个词,往往猝不及防地将你抓获。像一个时间的逃犯,你立刻被带回事发现场。你听见誓言的哀鸣,你再次看见,所谓过去从未过去。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这个日期被举起,被写下,因为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这个日期满载记忆而来,耳光般打在脸上。“正是”一词,饱含痛感。
“四月十七”这种直接明快的表述,与“正是”这类恳切鲜活的语气,可称韦庄词最能击中听者的要害所在。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收录的十八位词人中,温庭筠、韦庄列于卷首。温词富丽含蓄,深于韵味;韦词清丽明快,直抵肺腑。韦庄写词,与人推心置腹,倾谈之感因此而来。风格即人格,他首先是那样一个真诚而多情的人。
例如《菩萨蛮》五首组词中,“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如今却忆江南乐”,这些“尽说”、“只合”、“却忆”,都是很韦庄的表达。明快率真,读起来很过瘾。如果说艺术就是光明磊落,韦庄很个人化的表达风格正是:明月直入,无心可猜!
韦庄的真率并未伤害词味的蕴藉。细品之,“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尽说与只合之间,有多少曲折难言的心情啊。而这首《女冠子》的开头“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虽明白如话,然而多少心情、多少回忆由此决堤,汹涌而来。韦庄的明快,不同于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东坡的《念奴娇》虽豪迈,而所咏不过是历史的感慨,表达的形式和内容也都是散文的,并没有多少诗意。李清照在《词论》中说词“别是一家”,并对东坡词略有微讽,除了批评其词不谐音律之外,亦因东坡词豪放发论缺少蕴藉从而失却了词之为词的本色。
韦庄接着说:“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别时情景,宛在目前。“佯低面”,“半敛眉”,已可人怜,被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则更为可怜,化成一种美。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
据说羞色是爱情中最美的色。据说作为一项天赋,爱情业已失传。
《簪花仕女图》(局部)。
昨夜我梦见了你
《女冠子》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
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
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
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梦见她,不止一次了。上首《女冠子》词中说“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岂非倩女离魂?“除却天边月,没人知”,只有月亮作证。月亮将他的孤独嵌在一个无用的多情中。
这首词的写作应当就在四月十七前后,写于夜里梦见她的翌日。“昨夜夜半”、“分明”,又是韦庄句式。为何昨夜我梦见了你?梦中愈分明,醒后愈失落。“语多时”,梦中体验的时间,远非钟表所能指认,正所谓“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更有黄粱一梦、南柯一梦等,片时梦中,历尽一生。
古典文学写梦颇多。作为神秘的意识活动,梦既能与现实人生形相对照,更能将有限时空对人的囚禁,延伸到不可知的无限时空。而人通过对梦的思考,也可触及对人生本质的觉悟。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庄周梦蝶,梦醒之际,不知庄周之为蝴蝶与?蝴蝶之为庄周与?其间深藏生命的秘密。
“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人于梦中所见,多数时候影影乎乎。韦庄此梦,却异常分明。所爱之人眉目笑语,一如平生。她的神态亦活灵活现,“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如此真实,几乎触手可及。如果这个梦不醒来,那会不会变成另一种现实,如唐传奇中倩女离魂的故事?
然而,梦总有醒的时候。或许所谓现实也不过如庄子的猜测,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如果死后醒来,发现一生不过是做了个梦?人在梦中大多不觉是梦,梦中所历无异醒时,不过常常更突兀或模糊些,然而即便如此,方其梦时依然不知是梦,只有醒来才发觉方才是在梦中。如果将此体验推之生死,所谓活着不也很可能是一场自以为不是梦的大梦吗?比起“现实”,《庄子·齐物论》所论则更为真实:“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梦不知醒,醒不知梦,今不之后,此不知彼。无常,或许才是人更为本质的现实。
“觉来知是梦,不胜悲”,原来只是个梦。梦的真切再次遥远了现实的距离。昔日所爱到了分明入梦,大概在现实中已绝无相见的可能。
一启始就完结了的爱情
《荷叶杯》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
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
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
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顺着词中吉光片羽的闪回,我们隐约看出一个爱情故事的轮廓。若非亲历,孰能写得如此简洁而真挚?
韦庄另有一首《荷叶杯》:“绝代佳人难得,倾国,花下见无期。一双愁黛远山眉,不忍更思维。 闲掩翠屏金凤,残梦,罗幕画堂空。碧天无路信难通,惆怅旧房栊。”两首《荷叶杯》与两首《女冠子》,作为文学作品,虽不必确指,然可大致认定其所咏乃同一段感情。
虽然寥寥数句,这段情事却很完整。如何开始,如何结束,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上阕写如何开始,下阕写如何结束。中间的情节呢?没有中间,也没有情节。爱情的种类纷繁,一启始就完结了的爱情最多。这样的爱情是绝望的,因此愈加美丽。一开始就看见了结局,却仍然要开始,不顾、不信自己已被一个结局套中,所以说爱情是一种英雄行为。
或许有些人不会看见那等着他们的结局,比如词中信誓旦旦的这对恋人。谢娘者,美人也。夜半无人,垂帘私语,携手相期,指星誓水要在一起。然而随着天亮,世界在晨光中粗糙而真实,昨夜之事变得虚幻。晓莺残月,多么像一个惨淡的结局。相携的手不得不分开,因为天亮了。天亮之后,人得回去做人,回到命运的齿轮。或许的确因为地球在转动,人和人才会相遇又分开。
爱情很短,遗忘很长。“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初识情景历历在目,但那年是哪年?“记得”又是一个多么遥远的词。昨天一旦过去,一旦没有明天,昨天便已是一百年前。
“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从那年到如今,彼此已历多少轮回。已成异乡人的他们之间,不仅有时间的距离,有空间的距离,更有距离外的距离。正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这个故事耐人深味之处,还在于当初抱着别后重逢的希望,没有结果的结果后来才被认识到。或许各自为生活所迫,终成陌路,终于相见再无因。如同一场持续的滑坡矿难,待到察觉已成废墟。不是没想过你,而是忙于生活,更多时候想着自己。也不是没想过改变,而是妥协于现实和习惯,于是,最终适应了没有彼此的人生。
那夭折的爱情,变成一个洞,以悲哀的目光凝视你,讽刺你。什么也不能挽救,挽救了或也无处安放,唯一能做的就是写点儿什么。比如写诗,以此悼念,以此寻求些许安慰。
北宋黄筌《苹婆山鸟图》。
填词,我是“认真”的
文人填词之风始于唐中叶,至晚唐五代而盛。西蜀、南唐作为当时两大文艺中心,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人词客”。由此称谓即可看出,“客”者,意即填词并非文人的主业,主业仍是写诗。填词仅为业余爱好,涉猎客串而已。写诗才是正经事,文人的真实人生都写进诗里。词专为女乐演唱而填,所以那时文人填的词被称作“诗客曲子词”。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此乃确论。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写故国之思与人生无常,他的确将词的题材和境界扩大到更深刻的范畴和更普遍的体验中。词已不再专为女乐而作,词也可以写诗之所写。
韦庄词不同于花间诸词人之处,除了极具个人风格的表达方式之外,还在于他把自己的真实人生写入词中。当时别的文人填词基本上都属于“伶工之词”,即为了交给女乐歌者演唱而写,故多拟女子口吻写其闺情愁思。《花间集序》中所谓“为清绝之词,以助妖娆之态”。以此之故,五代词文辞固然清绝,配曲演唱想必亦很销魂,然而内容却因太题材化而不够真诚。
韦庄词在美学风格上仍不出花间范畴,但因为他以词写自己真实的人生体验,措辞明快,语气诚恳,情感真挚,因此可以说他是第一个“认真”填词的诗人。别的花间词写情美则美矣,然而多数面目不清。即使后来的柳永写“针线闲拈伴伊坐”,或是“烟花巷陌,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之类,也始终流于肤泛,而没有韦庄词中如此刻骨铭心的爱情。
撰文|三书
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