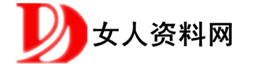自孔子将圣人君子塑造成道德主体的人格典范后,古代中国立志期许成为圣贤者代有人出,数量不少。他们在学术、心态以及行动方面以圣贤为模范,表现出浓厚的“圣贤情结”,奠定了圣贤君子在儒家传统的非凡意义。但真正被推许为圣人的则屈指可数,扬雄是其一,不过并不为人熟知。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或作杨雄,字子云,成都人。为成为圣人夙愿,扬雄曾拟《周易》而作《太玄》、拟《论语》而作《法言》,被王充《论衡》、桓谭《新论》等推许为圣人。《学行》作为《法言》的首篇构建了“学行成圣”的修养体系,是扬雄最具价值的思想之一。
扬雄对人性的认识超越了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他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即人在本性上包含善和恶相互混杂的两方面因素,“修善为善”“修恶为恶”强调了师者模范作用的重要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最终是善的还是恶的,和他们师从的老师与自身的修习关系密切。为此,扬雄曾举例说:“庄周、申、韩,不乖寡圣人而渐诸篇,则颜氏之子、闵氏之孙,其如台!”(《法言·问道》)颜氏之子即颜回、闵氏之孙即闵子骞,二人在孔子弟子“四科十哲”中以德行最受推崇,扬雄认为假如庄周、申不害、韩非等诸子百家能够不违弃、不轻视圣人即孔子而深入践习孔子思想,也许连颜、闵二人在德行方面恐怕也未必能奈何他们,即其君子人格形象恐怕连颜、闵都难以超越。
面对西汉末期动乱的社会现实,扬雄提出择师“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法言·吾子》)的主张,即师者如果是在世圣贤,其高尚人格可作为学习之榜样,此时师者形象可以直接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受学之人,这是最有效的教育方式,荀子说过“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荀子·劝学》)。荀子后面的一句话提示了另一种受学方式,即假如师者不是在世圣贤,则可由前世圣贤所存言论、事迹即“经”作为师者模范,扬雄认为这也是可行的。
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关键在如何落实践行,“睎骥之马,亦骥之乘也。睎颜之人,亦颜之徒也”(《法言·学行》),“睎”有远望、羡慕之意,扬雄将之升华为具体的修养学习方式,并以颜回睎于孔子而成复圣,正考甫、公子奚斯睎尹吉甫创作《周颂》而校正或创作《商颂》、《鲁颂》之例来说明。扬雄本人在择师入门方面无疑是幸运的,在蜀中生活期间他遇到两位思想开放、视野广阔的老师——林闾翁孺与严遵,其中严遵是西汉著名道家学者、思想家,后来扬雄十分怀念在“横山读书台”,即严遵门下的求学时光,可见严遵作为师者模范对扬雄的深刻影响。
成为圣贤君子或者士师这样的丰碑式人物,除学识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将行即德行加以落实践习,实现学行的统一。《法言》开篇《学行》的首句便是“学,行之,上也”,即“君子强学而力行”(《法言·修身》),扬雄这种学行合一的主张受到了孔子的影响,《论语》开篇《学而》的首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孔子对学之所得经由践习来适时加以落实验证的赞许,“自爱”“自敬”则是学之所得在道德层面的落实,但孔子本人只是强调了个体人格的道德自律及自我完善的必要性,即“内圣”的一面,如《论语·学而》篇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孟子认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章句下》),扬雄受此启发借鉴《老子》“其事好还”的观点,捋顺了其中内外先后的逻辑关系,即要想得到他人的爱敬,必须以“自爱”“自敬”为前提。《法言》类似的表述还有“先自治而后治人”“自后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等等。
扬雄学行合一成就圣贤的修养工夫和理路,远承孔孟传统,昭示人们超越凡俗进入圣贤君子人格建构的桥梁与途径。他同时将这样的机会赋予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让他们的生命主体意识得以高扬,启发他们在圣贤君子人格建构的过程中,在完善个体作为道德主体和智识主体的“内圣”因素外,自觉切实担当起对家国天下的关切,光大圣贤君子人格的社会主体责任意识的“外王”因素,这是扬雄思想非常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