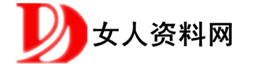1:你是怎样上你太太的
正如励扬猜测的一样,乐恒里在审问杨桐的时候遇到了僵局。
对于作案现场是否存在“第三人”,杨桐始终保持沉默。
技术科的同事发来一份报告,通过分析监控视频,温澄那天在电梯里遇到的保洁工人,确实是一个身高约180厘米的男人。但因为男人戴着帽子,监控并没有抓取到男人的面部特征。
虞琳把这个消息告诉温澄。
温澄思考一番:“我觉得可以继续从明宸身边的人查。”
另一边的乐恒里也正想到这一点,既然能从七年前的一桩自杀案查到杨桐和林子祥,说不定还能顺藤摸瓜查到明宸牵涉到的其他案子。
……
办公室里挂着的电子时钟,显示现在已经接近九点。
温澄目光微凝,她彻底错过了今天的堂议。
她现在是回江湾壹号还是回玉兰公馆?
在此刻,温澄心里萌生了从来没有过的退意。她站起来往外走,心里叹一口气。
她需要回玉兰公馆,去确认一件事。
尽管她心里已经对答案有九分确信。
“乐恒里很在意你。”虞琳默默地把温澄送到警局门口,看着她披着的外套说道,意味深长。
温澄顺着虞琳的目光,意识到她此时还披着乐恒里的衣服,抬手默默把外套收下来。
“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有点、有点好奇而已。”虞琳又把外套重新给温澄披回去,现在室外温度可能只有10℃出头。
虞琳的耳廓肉眼可见地红起来,她摸了摸鼻子,不知道怎么继续接下来的话题。
温澄多多少少能看出她的心意,忽然开口解释:“我和他是高中同学,很多年没见了,等案子结束之后,也不会有什么交集。”
“呐……乐恒里他……哎。”虞琳罕见地结巴起来,最后闭上了嘴。
温澄把外套脱下来交给虞琳:“我先走了,麻烦你交给他,谢谢。”
-
回到玉兰公馆时,晚宴已经结束,熙熙攘攘的温家又恢复成往日的清冷氛围。
走在白玉兰道上,温澄一路低着头,思考今天接收到的所有信息。正在出神之时,她听见前方传来一阵轮椅碾过地面的声音。
静谧清冷的夜里,声响格外清晰,一团人影由远至近。
温澄隐匿在一道树影下,注视着不远处的少年把坐在轮椅上的温山搀扶上车。
温山的面色被少年的身影挡着,意味不明,但身影却十分的颓靡。
少年是温山的小儿子,在温家孙辈排行第八的温玉珩。
温山的妻子梁偲穿着一身流光溢彩的旗袍,却衬得脸色惨淡,精致的妆容掩盖不住岁月的褶皱,反而显得有些刻薄。梁偲披着羊绒披肩,与温玉琢相互搀着,一老一孕,在萧瑟夜风中显得有些弱小。
站在一旁的温玉言更是面色不虞,额头上还一处包扎的痕迹,他嘟嘟囔囔嫌温玉珩的动作温吞,随即转身离开上了另一辆车,后面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跟着他,应该是他的妻子。
大房一家子分别上了三辆车。
温玉珩上车时,无意中看到了远处的女人。他还是高中生,明天不是休息日,所以单独上了辆小轿车,准备回私立高中的寝室。
他问:“那是七姐姐吗?”
站在旁边的管家细细辨认,点头答道:“是的,八少爷。”
前面两辆车疾驰而去,大房几人都没注意温玉珩又下了车,此刻正朝温澄走去,微躬着身体打了声招呼:“七姐姐晚上好。”
这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说话,虽然今早在堂议时,他远远地看了一眼这位堂姐,面相和气质都与家里其他几位姐姐很不一样。
看来他是个懂礼貌的孩子,真是出淤泥而不染啊,温澄想道。
“玉珩。”伸手不打笑脸人,况且还是个高中生。温澄朝他点点头,打量这个与她差不多高的孩子,面颌微方,戴着一副方框眼镜,虽然穿着一身精致贴身的西装,却掩饰不住他那股学生气。
“天气冷,七姐姐赶紧回去暖暖手吧。”温玉珩转身陪她走了一小段路。
温澄:“你现在在哪里读书?”
“我在诺安国际学校念高一。”温玉珩乖巧回答,直直地盯着她,似乎很希望她继续问下去。
温澄点点头,称赞这是所不错的学校,便没再说话。
走到小红楼门口,温玉珩仍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你早些回去休息吧,毕竟明天还要上课。”虽然没有恶意,但温澄对这个素不相识的八弟仍有些警惕,甚至在思考他看自己的眼神,是不是稍微有些炽热了……?
温玉珩转身走了两三步,又退了回来。
“怎么了?”温澄古怪地看着这个去而复返的堂弟。
“七姐姐,你是不是认识、认识J大的祁琚教授?”温玉珩脸色微红,目光有些闪躲。
“……”什么情况?温澄有些犹豫,刚想回答认识,就听见一声嘲弄——
“她不止认识,还熟得很。”温渟那道熟悉的声音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有人替她回答,温澄挑了挑眉,转头看着来人。
温澄没想到,温玉珩竟然有些害怕他这位长辈,支支吾吾喊了声五叔就溜了,脚步快得像逃命似的。
和他刚刚对自己的示好态度大有不同。
“诶,温玉珩你跑什么呢?”温渟对着消失的人影喊,一只手随意搭在温澄的肩膀上,似笑非笑地问:“我有这么可怕么?”
隔了一秒,他又对着温澄问道:“你怕我吗?”
温澄无情地把他的手打下来,斜着看他,“是个人都会怕咬人的疯狗。”
她把温渟比做会咬人的疯狗。
温渟直愣愣盯着她,没有感情似地轻笑一声:“这也不怪温玉珩会怕我,毕竟今天他亲眼目睹,我是怎么把他那个断腿的老爸——挑——下——台的。”
温澄愣了愣,顺着他挑起的话头接着问:“看来你今天在堂议上赢了温山?”
“呵,”温渟勾起唇角,得意地嗤一声,“难道我还能输?”
“……”温澄无语。
温渟安静几秒,收敛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情,对她说道:“怎么不接着问了?”
“我大概都猜到了,”温澄接着往小红楼走,“你能这么快得找到长华的供应商合同,是不是早就开始在查大房了?”
“嗯。”温渟没有多言,神情傲然。
“明宸在温建贪了五十亿,大半都通过供应商的路子进了温玉言的口袋里,你在堂议上把他们贪/污的证据都拿出来了?”温澄平静地问。
温渟点头,又扬扬下巴示意她继续说。
温澄接着道:“温玉言当然不肯认,所以温玉言把所有事情都推到已经没办法再说话的明宸身上,当场就和明家撕破了脸?”
温渟向她投去一个赞许的眼神,默认她猜对了。
如果温玉言在堂议上认下这个污点,大房除了一个还没成年的温玉珩,没人再能顺利地成为温山的接班人。一旦温玉言在众人面前失格,温山这些年所做的一切都会前功尽弃。所以无论真相如何,温玉言都会把贪/污这件事甩开,但在温渟的证据下,温玉言没办法彻底洗清自己的嫌疑,只能把整件事情推给明宸,假装自己不知情或者是受到明宸的蒙蔽。
明家失去一个儿子,又在堂议上被人当场揭穿劣行,怒不可遏,把温玉言做的那些污糟事情都抖落出来。
“何止撕破了脸,就算温玉琢怀着明宸的儿子,怕是没法再回到明家了。”温渟想起温玉言和明家互相推诿的场景,显然有点幸灾乐祸。
今天温思俭动怒,甚至将一直不离手的拐杖都扔到温玉言的头上,磕出好大一个包。
“你对一个孕妇也这么狠么?”温澄淡淡地问。怪不得大房一群人离开玉兰公馆时,身边只有几个仆从和管家,几乎没有人出来送别,和以前进出张扬的样子大相径庭。
温渟没想到她会问这个问题,思考了三秒钟才回答:“她的出身,即是原罪。”
温澄抬头,对上他的目光:“所以我作为温渊的女儿,被牵扯到这场案子里,也是我的原罪吗?”
“——出身在温家,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温渟语速缓慢,“不光是温玉琢,就连我和你,还有温慕卿。”
听见这个久违的名字,温澄和温渟对视一眼,很快就没了声。
夜晚静谧,只有小红楼里传来的细碎人声,还有对面马路上的汽车鸣笛。
温渟失去调侃温澄的兴趣,转身离开。
与温澄错身时,他低声道:“今天的堂议,温峙以你和明宸的案子还有牵连作为理由,把你革职了。正好我的淞旅控股缺人,你下个星期就来我这儿干活吧。”
温澄眉头一蹙,上前拉住温渟不让他走,刚想问这是怎么回事,却看见小红楼里走出来一个老妇人。
白姨看着温澄身影单薄,裹挟满身寒意,于是把自己批着的毯子颤颤巍巍地盖在她身上,恭敬道:“七小姐,四爷有请。”
温渟听见这个苍老的声音,转过身,罕见地收起自己混不吝的气势,对着老妇人喊了一声“白姨”。
“四爷,好久不见。”白姨平静地和他打招呼,却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便带着温澄往小红楼里走。
温澄莫名顿住,一个走神的功夫就被白姨带到温渊在三楼的套间。
“白姨?”温澄认出这个老妇人,顺着温渟的口吻也唤她一声。她曾经在温渊住着的老式洋房见过这个老人家,温澄之前以为她只不过是个资历较深的管家,没想到还有点来头?
白姨停下脚步,侧身朝着温澄,双手交叉在身前,以一种缓慢却不会让人觉得费时间的语调回道:“七小姐。”
温澄把毯子还给她。
她已经满头白发,但梳理得一丝不苟,额边没有丝毫掉落的碎发。略宽的额头给她增添了些平和的气质,细致的眉眼、高挺的鼻梁无不彰显着她年轻时是个美人,就连脸上的纹路都恰到好处,沉默地诉说着沧桑的故事。
“我姓白,是六小姐母亲周氏的乳母,前些年一直在英国陪着六小姐,所以大家都喊我一声白姨。”白姨接过毯子后,看出她的困惑主动解释。
原来是周浣玉的乳母,温澄微讶地点点头,她知道温慕卿年少时曾经在英国跟着温渊生活过一段时间,直到确诊之后才返回国内定居治疗。
“七小姐,四爷无论做了什么,都是为了您好。”白姨又缓缓地补充道。
温澄脚步刚到门口,准备敲门,听到白姨的话,心里突然升起一丝犹豫,她不解地看向白姨,却只见到白姨望着远处,似乎又想起了故去的温慕卿,神情寂然。
-
门是虚掩的,温渊的声音从里面传来:“进来吧。”
温澄推门进去,直接坐在温渊斜对面。
这还是她第一次看见温渊这么休闲的一面。
温渊已经洗漱过,头发微湿,穿着一件居家的墨色绸缎睡衣,袖子挽起到手肘的部位,他拿起桌子上的半框眼镜戴好,用指尖推了推镜片边缘,确保戴正后才透过镜片看向温澄。
见她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显然刚从外面回来。
白姨贴心地把门关上,给这对父女留下私密的空间。
温渊:“见过温渟了?”
温澄喉间发出一声嗯。
“他和你说了?下个星期你去淞旅控股,”温渊又问,看见温澄继续默认,他补充说,“淞旅控股接下来有好几个大项目,你都可以接手,比温建的工作更加有趣。”
“你和温渟,在做交易吗?”温澄问完,自己心头也猛地一跳,她居然下意识用“交易”来形容他们之间的这场游戏。
温渊反问——“什么交易?”
“你帮温渟,把大房踢出温建,温渟作为回报让我进淞旅控股。”
温渊平和地笑笑:“后半句说错了。温渟让你进淞旅控股,是真的看上了你的能力,而不是我帮他的回报。”
沉默两秒,温澄低声说:“所以,你一直站在温渟这边。”
“我只能选择温渟,”温渊没有否认,“大房贪污的那些证据,大部分都是我提供的。”
老爷子想把他唯一的女儿树成温建的枪靶子,他现在做的不过是把火力从温澄又引回到温渟身上。不过,温渟也不排斥自己变成新的靶子,毕竟这些攻击本来就是属于他的。
令温渟出乎意料的是,温渟似乎对温澄没有敌意……也许是因为温慕卿的关系。
温澄问:“你在大房安插了人?”
“嗯,就像明宸安排杨桐在你身边,温玉言安排行政助理在45楼监视你一样,安插人很简单。”
温渊对温澄身边的人了如指掌。
温澄原本平放在膝盖上的手微微蜷起,三秒后——
她声音平静,面无表情地问:“杨桐真的只是明宸的人吗?”
“只是”这个词微妙而又充满试探性。
周遭的环境像被人摁下静音键般安静了将近一分钟。
温渊忽然出声问她:“你怎么会这么想?”
没有否认,而是问她为什么会这么想。
温澄的心凉了半截。
她沉默半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尽可能得平静:“我的直觉——”
说出这四个字后,温渊打断她接下来的话:“不是直觉,是这么多年来,你已经养成了一套优秀的思维逻辑。在得到无序的线索后,你会下意识地思考,在抽丝剥茧后得出结论。”
此刻,男人幽黑的眼眸注视着他的女儿,以命令式的、不可抗拒的语气对她说:“告诉我,你的结论是怎么得出的。”
……
温澄一向很注重自己的行程私密。
特别是在出国后,她尤其介意别人透露自己的隐私信息。
可能是因为少年时期曾经遇到几个……奇葩,譬如一言不合让她掉进水库的乐恒里,或者是玩了两回强/制/禁/锢的岑让。
她在欧洲时,也因为华人身份遭到过不同程度的骚扰。
温澄在杨桐成为自己的助理后,曾经义正言辞地强调过——除非她允许,杨桐不能把她的行程随意告诉任何人。
而就在温澄第一次把祁琚带回江湾壹号的那天,温渊在工作时间段登门,显然知道她在家里。
那时温渊刚回浦淞,质问她为什么要进温建。
温澄记得,温渊刚进门时就开口解释是从杨桐那得知她在家。
她当时就皱了眉,尽管温渊是她的父亲,温澄也很介意杨桐泄露她的位置。
更何况她当时正和祁琚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一番折腾下来,温澄对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格外的印象深刻。
今天在警察局坐了一下午的冷板凳,她忽然间就想起这件事情。
现在想来,杨桐之所以会把自己的位置告诉温渊,并不是因为一时疏忽,而是杨桐一直效忠的人就是温渊,所以才会毫不犹豫地把有关于自己的信息都告诉了温渊。
他们也许在很久之前,就有了联系。
早上在蓝山咖啡馆,温澄在杨桐对面坐下后就下意识地表达自己的疑惑——“你知道我今天的行程?”
显然杨桐早就知道她在玉兰公馆,所以才能约好在公馆对面的咖啡馆见面,并且在十分钟之内就抵达还点好了一杯咖啡。
杨桐解释她是从新助理口中得知她今天的行程,后来温澄向颜溪求证,颜溪否认她把温澄的schedule告诉给了杨桐。
颜溪算得上是温澄的老友,毕竟两个人在英国一起干了好几个项目,无论是作为她的朋友,还是助理,颜溪都知道她的底线,其中一条就是不能随意向别人泄露她的行踪。
那么,杨桐是怎么知道她今天要回玉兰公馆参加堂议会的呢?
如果不是查到了杨桐姐姐杨榛的资料,温澄不会往温渊身上想。
杨桐和杨榛都曾经是J大的学生,杨榛是外语系的优秀毕业生,身处于一个很容易和温渊产生交集的专业。
温渊因为工作关系,经常需要在中国和英国之间飞来飞去。杨榛七年前自杀去世,在J大闹得沸沸扬扬,还和明家的太子爷明宸有关,温渊难道一点都不知情吗?
如果他知道这件事的话——
-
听完温澄的推测,温渊拿起桌子上刻着精致花纹的玻璃杯,察觉到水已经凉透,他又松开手,转而给自己倒了点热水。
“你猜的没错,我确实在杨桐进入温建前就认识她。”温渊说完,一饮而尽杯子里的温水,尽管水的温度还没被中和到一致,忽热忽冷,“她和姐姐杨榛的感情很好,所以她愿意为杨榛牺牲一些东西。”
他当年只不过是稍微提点了杨桐,给她一条能搭上明宸的路子。至于杨桐后来做出的事情,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杨桐的人生,就这样被温渊轻飘飘地定义成为隐晦的“牺牲”。
温澄的指尖深深嵌入柔软的手心,她忍不住继续问:“那今天也是你让她约我出去——”
“是的,是我拜托她约你出去。不出所料,今天警察就会查到她,然后把你也顺便带走。”温渊并没想到,警察之所以能查到杨榛,是因为温澄无意中对乐恒里说的那句话。不过退一步来说,如果警察的工作效率真的低到不行,在下午的堂议开始前还不能查到杨榛身上,他也会主动把线索送上门。
“被警察带走以后,我没有参加下午的堂议,只能被二房踢出温建,温渟顺势让我进了淞旅控股。”温澄说完,揉了揉发涩的手腕,从坐下伊始,她的左手就一直维持着反手的姿势,撑在沙发上的姿势太久,造成一点不适。
“我说过,你不能在温建。”温渊说。
如果温澄不听话,他只能采取一些手段让她离开温建。
温澄低头,她轻笑一声,“那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台宾利被温玉言动了手脚,于是你顺水推舟,让杨桐自导自演出一场戏,是吗。”
“嗯?”温渊偏过头,平静的目光落在温澄身上,终于泛起一丝波澜。
“这些年,温思俭早就知道大房和明家串通起来,通过上下游供应商抽成温建的油水,但他一直隐忍不发,不仅因为明家在浦淞的势力,更因为大房在温建根基深厚,想要连根拔起必定会造成高层人员的动荡。”想要改变温思俭对大房的容忍态度,一定要等待时机,挑战温思俭的尊严,侵犯他的利益。
温澄一动不动地看着温渊,继续说:
“但是在这个家,还没人敢直接冒犯温思俭。当知道温玉言在我的车上做了手脚,你知道这是一个暗示温思俭的好机会——让他知道,大房能通过长华在我的车上做手脚,有一天也能够以同一种方式伤害他最心爱的温渟,甚至是他自己……”
温澄的话还没说完,温渊已经变了脸色,眉心微微皱起,深黑的眸中闪过一丝不悦。
很快,温澄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凝视着眼前的男人淡淡一笑,嗓音已有些沙哑,最后问道:“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明宸的尸体会出现我的车里。”
温渊盯着她许久,摇了摇头:“这是个意外,”他似乎重新认识了一番这个女儿,缓缓说道:“最迟明天,明宸的案子就能了结,不会再牵扯到你。”
1:你是怎样上你太太的
温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的公馆。
等她回到江湾壹号后,已经过了零点。
她神思恍惚地蹲在花洒下,双手抱着肩头,任凭充盈的热水用力冲刷她的身体。
热水顺着额头滑入她的眼,可她却不知道疼,一直睁着眼,盯着淌过的水。
……
祁琚在实验室熬了一天,神色有些疲惫。
走到J大停车场时,他看见黄叔守在自己的车旁,微微讶然。
祁琚已经很久没让黄叔接送自己了,上一次见到他还是过年的时候。
“小琚——”黄叔看着眼下微青的男人,不免有些心疼,连忙给他开了车门。
祁琚揉了揉眉间,问:“黄叔,您怎么来了?”
“祁总说您这些天辛苦了,让我送了点补品过来,还有一份文件。”黄叔给祁琚开门,顺便把祁建辉叮嘱的一份文件袋递给他。
“是什么?”好不容易从实验室里出来,祁琚现在看到任何一张纸都有点头疼。
“祁总说是有关于皖南温家的资料。”
祁琚动作一顿,随后打开文件袋的速度变得更快了些。
“对了小琚,今晚是回祁家还是——”
“去江湾壹号。”
黄叔从后视镜里看见祁琚的面色一点点沉入深渊,不自觉地踩了踩油门,把速度加快。
半个小时后,祁琚终于回到了温澄那栋小复式。
一楼的灯是关着的,门口的感应灯亮起,铺满一小片暖黄的光。
温澄的高跟鞋甩在地上,一只正着,另一只歪倒在地上,鞋跟堪堪擦在墙上。
祁琚弯下腰把她的鞋摆好在边上。
担心她已经睡着,他摸黑上了二楼,没有开灯。
主卧的门虚掩着,透出一丝光亮。
门缓缓被推开,祁琚逐渐看清室内,微薄的光亮都挤在角落的浴室里。
浴室在主卧的角落,用玻璃隔开,朦胧的光影映射在木地板上,透出一室水光潋滟。
大灯没开。
浴室里没有声音。
床上也没有人。
-
女孩坐在落地窗前,低垂着眉目,似乎置身于一片寂荒之中。
似月光般的绸缎,随风飘芜的裙尾,残影斑驳,任由透明的玻璃挡住所有温度。
孤月的光恰好捉住她的脚跟。
微风凉透了她手里的酒。
这一刻,她只像一个无助的孩子。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才注意到来自门边的凝视。
“……祁琚?”她的声音喑哑,像一盒年久失修的录音带。
祁琚握在门把上的指尖微动。
他快步走向温澄,才注意到她披在肩上的毛巾。
头发半干,显然是还没有吹。
“怎么不吹头发?”祁琚温柔地揉了揉她的发顶,潮湿的水汽沾染他的手,连带着润湿他的心。
温澄仰起头看他,毛巾落在地上。
“你帮我吹吗?”
“好。”不管她说什么,他都会答应。
吹风机运转,扑起温热的风,吹散了温澄最后的隐忍和倔强,难以抑制的心痛从她的胸腔悄悄往上爬,逐渐占据了脑海里的所有理智。
祁琚跪在她身后,指尖穿过她的青丝,微震的吹风机和女孩颤抖的频率一致。
他关上吹风机,双手轻扳,把温澄转了个向。
两个人面对面,他伏下身子,平视她。
温澄感觉眼前弥漫着无法驱逐的雾,眼前的男人像雾中的月,仿佛只要日出了就会消失。
她顿了顿,竟然有一刻分不清此时是梦还是现实,只是在眼睫抬起的那刹那,泪珠像雪崩一样滚下来,大起大落地滴在她屈起的膝盖上。
祁琚在心中微叹,捧起她的脸,轻轻的、如信徒般虔诚的,吻上她的眼。
滚烫的泪微涩,涩进了他身体里每一处细胞。
如果今晚不曾见过他,或许温澄难受一阵就会爬上床,在混乱的思绪中度过难眠的夜。
但在他难以抵挡的温柔攻势下,她感觉自己像被大卸八块的螃蟹,手起刀落后只剩下柔软的蟹肉,再也没有能够抵抗世界的勇气。
温澄哭得悲痛又热情,那是祁琚未曾见过的样子。
等清醒过来后,她才发觉自己像一只八爪鱼似的缠在了祁琚身上。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祁琚已经坐靠在墙边,原本一丝不皱的衬衫像被人狠狠蹂/躏过,褶皱糟乱,布满点点泪痕。
如果气氛暧昧的话,这是一个会让人脸红的姿势。
但没有一个人往那儿想。
这只是一个纯粹的,充满依赖感的拥抱。
她抹了抹眼泪,摇摇晃晃从他身上爬起来,坐在他大腿上,像沼泽边一尾泥泞又破碎的芦苇。
两人对视,相顾沉默。
他的目光像是要把她看透一般,深黑的眼瞳像是夜里磅礴的海。
初以为是平静的海面,却能听见滔天巨浪翻滚的响声。
似深海里神秘的漩涡,渐渐把人卷进深渊。
“还哭吗?”祁琚伸手,指尖卷走她脸上最后一滴泪。
温澄摇头,经过猛烈的发泄,她的心情平复不少。
祁琚像哄小孩似的搂着她的腰,把她抱到一楼的厨房流理台上。
每走一步,都能隔着衣服听见他们轻微而又剧烈的心跳声。
祁琚给她倒了一杯水,又问:“吃晚饭了吗?”
温澄想了想才摇头,回想起光怪陆离的昨天,岂止没吃晚饭,连中午饭都没吃。
祁琚打开冰箱,打算做一份清汤面。
在他烧水的间隙,温澄就着厨房的水池匆匆洗了个脸。
祁琚抽出两张餐巾纸,轻轻擦拭她脸上的水迹,顺便低下头亲亲她的唇。
熟练顺手的样子让温澄感觉他们像一对老夫老妻。
“你不好奇吗?”温澄看着正在打蛋的男人,忍不住问。
好奇发生了什么,她为什么哭得那么猛烈。
祁琚把瓷碗搁在台面上,认真地看着她:“你要是想说的话,不用我问也会说。你要是不想说的话,我不会逼你。”
水开了。
他抓了一小捆挂面,似乎也遵循着精准测量的习惯,不多不少刚好是一个人的份,在沸水里搅拌完才低声说:“现在我只关心你饿不饿。”
哭泣是一件非常消耗体力的运动,温澄摸了摸肚子,是真的饿了。
而那些令她十分抑郁的事情,也像沸腾的水,逐渐熄了火。
五分钟后,一份非常清淡的挂面出锅了,唯一的油水是那个煎得十分规矩的荷包蛋。
温澄一边吃面,一边把最近发生的事情概括给祁琚。
祁琚看着她的眼睛,像被水洗过一般的干净透彻——如果能忽略掉那双肿胀的眼皮。
“你之前见过的那个女助理杨桐,她的姐姐被明宸侵害过,七年前自杀了。杨桐为了报复明宸,通过温渊搭线进入温建,成为温渊安插在温建的人。
杨桐把自己献给明宸,也是为了日后的报复。虽然杨桐作案表面看起来和温渊无关,但谁知道是不是在温渊的唆使下,杨桐才会用这么极端的手段报复明宸呢。
我今年进入温建后,明宸又把杨桐安排在我身边,可能是想在我这里捞到一些好处或者抓到些把柄。
但没想到,还没等他付诸行动,他就被杨桐反杀了。”
祁琚听着她平静的语气,虽然面色没有波澜,但心底早已掀起一场风暴。
他皱了皱眉:“听起来像碟中谍。”
温澄把筷子放下,叹了一口气,“可如果不是她的话,我可能会死于一场意外。”
祁琚脸色微变。
“杨桐的姐姐在死前有个爱人,叫林子祥,在长华当车辆维修员。之前我有辆宾利撞坏了,送去长华维修,有人下了命令,让林子祥破坏刹车系统,想让我意外身亡。杨桐知道这件事情后,没让我碰那辆车,又把这件事告诉了温渊。
大概是温家大房的人下手的,自从我进入公司后,他们就没落着什么好。温渊知道之后,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把柄,他没有第一时间揭穿大房,反而想放大、曝光这场未遂的阴谋。正好温渊和温渟联手一直在查大房这些年在公司的错处,使了手段让老爷子知道这些龌龊事情,又在昨天的堂议上彻底破坏了大房和明家的关系,终于让老爷子下定决心放弃大房。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连我自己说出来都觉得像是天方夜谭。明明大家都是出自一条血脉,却能把谋害、算计这些事情弄得明明白白的。更可怕的是,有些人自以为是执棋者,却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为了棋子,任人杀伐。”
说完,温澄抿唇,露出一个勉强的笑。
笑容还未消散,祁琚伸手握住她冷冽的指尖。明明刚吃完一碗面,但是她的手却怎么也热不起来。
祁琚慢慢拢住她的手,看着她的目光坚定而温情:“十六岁那年,我在新加坡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月。那年寒假,我爷爷急病去世,每个祁家人都想分一杯羹,而我们的处境复杂而又艰难,见识到的手段,可谓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面临很多没有意义又不可避免的人际拉扯,他们就像混入空气中的灰尘,避无可避。”
“但那又怎样呢,如果说我的人生像一趟列车,他们不过是未经允许上车的乘客,下一站到站后我就能把他们赶下去,说实话,我现在都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
“就算你出身在温家,也没有人规定或者要求你一定要成为他们那样攻于算计的人,保持本心永远比改变自我来的更重要,你可以继续追求你理想的,我永远都是你的退路。”
你是怎样上你太太的网友评论:
网友:陈客恋:下不为例!”陶歆再次强调。
网友:侯嬖裔:“夏族都很谨慎,让他们各自都完全分开,想要动手破坏都没机会。
网友:毛声逻:
网友:范妲涯:你怎么又来了?你真是阴魂不散啊,本座这才消停了十几年,你又来了,你、你想干嘛?”
网友:陈玖缨:自来也你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一次的对手是那个宇智波斑,不要忘记他那拥有强大瞳力的瞳术,在他的面前任何忍者都没有办法抱住自己的情报,他是不可能战胜那个家伙的瞳术的!”
网友:李脉荷:“断牙山脉,星光世界之主。
网友:杨惶:如果没有一点怀疑,血腥主宰说这些话倒也正常。